宿迁史志 | 《红楼梦》里的“打尖”,宿迁人今天还在用
“打尖”一词在宿迁方言中虽然被广泛使用,但它却是一个与其他方言区共用的方言词,并非产生于本土。它专指旅途或劳作中停下来休息吃点东西。停下来抽烟就说抽烟,停下来就餐就说就餐,只有停下来休息加吃点东西,即非正餐时间吃点东西并且稍事休息才是“打尖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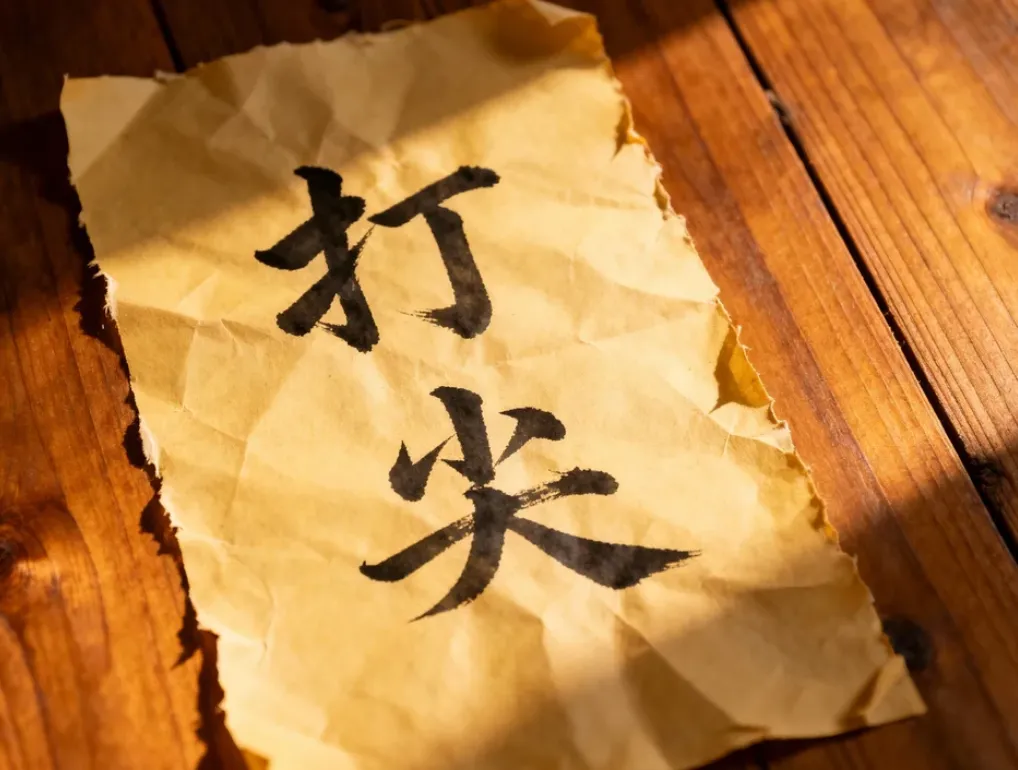
我国北方方言区有广大的区域使用“打尖”一词,意为歇肩,作短暂的休息,多数的用例都是指休息的时间吃点东西,比如背负重物登山,休息时不放下重物,为避免放下之后再背不起来或再背起来费力,多用登山用的木杖支撑重物,让肩头得到休息,趁这空档吃口干粮。似乎“打尖”之“尖”宜用“肩”。由此有人猜想,“尖”或许本是“肩”,取“歇肩”之意。

南方的一些方言区同样也有使用“打尖”一词的,比如人背、马驮茶叶在行程中,停下来休息吃点东西,假如所带干粮即为炒面,那么就把堆积在容器中的冒出尖的部分吃下,谓之曰“打”掉这凸起的“尖”子,恰是“打尖”的生动写照。正是恰如其“辞”,似乎这打尖之“尖”又宜用“尖”字最恰当。这南北之别,让“尖”字的取舍成了宿迁方言研究的趣味注脚。
虽然方言词中有时也使用同音替代,笔者非常同意使用“打尖”而非“打肩”,特别不能同意将打尖误解为停下休息拍打肩膀使血流通畅,笔者早年曾参与过农业生产劳动的项目——抬汪泥,肩头被扁担、木杠压出瘀血的红道道,麻木肿痛,汗水渗进伤口,衣衫都粘在肩上,揭起时疼得钻心,别说主动拍打,连碰都不忍碰,每次抬起一兜汪泥,肩膀都是疼痛难忍,心理和体力都承受着挑战,当揭起被汗水渗血粘连在肩头的衣衫时,更是针扎一般疼痛,怎么下手对肩头拍打呢?宁肯血流郁结肩头肿胀,也不愿拍打肩头而造成难忍的疼痛。所以“打尖”之“尖”不可以强解为“肩”。“尖”字的使用,本就与“拍打肩膀”无关。
宿迁人平时用的“打尖”一词有约定俗成的含义,无论是旅途还是劳作,宿迁人说打尖虽然有停歇的含义,却往往有意忽略这种停歇,而只侧重“吃点东西”的含义。这与南北诸多方言区的用法都有区别,而与古籍的用法却完全一致,可见有其传承的“正统意义”与古人的“书面意义”不谋而合,藏着语言传承的密码。
例如《红楼梦》第十五回:秦相公“忽见宝玉的小厮跑来,请他去打尖。”

贾宝玉和秦相公
这时的宝玉与秦相公本在休息的途中,所谓打尖只是吃点随车带来的点心食物等,小厮请宝玉去打尖,其核心意义只在“吃点东西”,与“停车休息”同被限定在“打尖”的程序之中。《红楼梦》中“打尖”一词的使用与宿迁人方言中使用的“打尖”完全相同,宿迁人读来理解方便、容易、毫无隔阂。而反观一些文献与工具书的误释,更显得宿迁人用法的珍贵,其它古近先贤使用的“打尖”往往在休息或吃点东西的问题、事件界定上有意义理解的出入,导致一些通用的词语工具书也难以规范界定“打尖”一词的意义。例如:
阿英《滩亭听书记》:“说至一半,则稍停以间之,曰打尖,亦曰小落回。”这里的“打尖”则泛指停止、间隔、休息,没有稍停进食、进饮水的含义。
清人福格《听雨丛谈·打尖》则说:“今行役于日中投店而饭,谓之打尖。”这应是对打尖一词的明显误释。因此《辞源》也误释打尖:“旅途中休息或进饮食”,却忽略了短暂的时间概念和劳作的概念。根据古今使用“打尖”一词的正确例证,显然都有“时间短暂”的限定,不包括“投店而饭”“投店餐饮”和“打火做饭”。《辞源》中的“旅途中”对此语焉不详。还都漏掉了“短暂”与“非正餐”的关键限定。
又如《镜花缘》第六十六回:“小春道,‘你要飞车何用?’婉如道‘俺如得了飞车,一时要到某处,又不打尖,又不住店,来往飞快。……路上又快又省盘费,岂不好么?’”从此例中不难看出,《镜花缘》基本明确了“打尖”是在途中暂停“休息或进饮食”,因此导致路上“不快”了,如果是“住店”打火用餐,无所谓“快”与“不快”,只能是婉如对“盘费”问题的考量、计较了。《镜花缘》里“不打尖,又不住店”的表述,明确“打尖”是途中短暂停食,与“住店正餐”泾渭分明,恰与宿迁方言和《红楼梦》的用法呼应。
这些用法、意义的不同,难免导致辞书的释注语焉不详。但凡使用“打尖”一词能够真正和《红楼梦》中的用法一致,与宿迁方言中“打尖”一词意义相同的应该被确定为“打尖”一词的最原始本真的意义。例如:
在劳作中休息和吃点东西。李瑛的诗《红旗道班》云:“累了,来歇脚;饿了,来打尖。”诗句中的“歇脚”和“打尖”互文见义,分别指在短暂停歇中缓解累饿的行为,显然不应指收工、住宿和做饭、用餐的“大”动作。
在旅途中休息和吃点东西。姚雪垠《李自成》:“倘若在平时行军,遇着这样好的地方,应该命人马停下来休息打尖,然后再走。”这一例更说明了停下休息打尖都是短暂进行的。
“打尖”是旅途、劳作中短暂的停憩进饮食,不能包括“打火做饭”的“投店餐饮”。成书于《听雨丛谈》同一时代的《镜花缘》在使用“打尖”一词时却有别于《听雨丛谈》的用法。如六十三回:“即如路上每逢打尖住宿,那店小二闻是上等过客,必杀鸡宰鸭,谆谆馈送,无论早晚,处处皆同。这位姐姐因无故杀生,颇觉不安,到处命人劝阻。”店小二的杀鸡宰鸭,除满足“上等过客”“住宿”食用之外,还“馈送”路上“打尖”食用。可见,“投店而饭”多为正餐,与路上“打尖”的“吃点东西”还是有区别的。虽然“投店而饭”也属在“旅途中休息或进饮食”,但在时间上却不是短暂的。

旅途中饮食
宿迁人使用的“打尖”一词的方言意义和《红楼梦》中“打尖”一词的实际意义极易被一些不同的使用意义所搅混。因此有些其它文献中使用的“打尖”在意义的正确性上还是有必要进行辨析的。前文《红楼梦》第十五回的打尖句例所言,后文便得以证实:“家下仆妇们将带着行路的茶壶茶杯,什锦屉盒,各样小食端来,凤姐等吃过茶,待他们收拾完备,便起身上车”,“一时上了车”,“车轻马快,一时展眼无踪”。可见这“打尖”只是停下休息进饮食,不是进店住宿餐饮。
“打尖”在宿迁方言中的独特运用习惯,具有含义与语法的双重特质的鲜明沉淀。其一,含义清晰。虽含“停歇”之意,却更强调“吃点东西”的核心语义,与《红楼梦》的用法一脉相承。其二,语法规范严谨。宿迁方言有爱使用“子尾”的特点,但“打尖”从不加“子尾”—— 一旦说成 “打尖子”,意义就变了,如“优等生被城里学校打尖子了”,“打尖子”就成了“掐尖子”的同义语,指挑选优秀者。至于“爪夺尖子”(自我突显)、“冒尖子”(突出显现)、“削尖子”(打击尖子或充当尖子)等,这些带“子尾”与“尖子”有关的方言词的用法显然都与“打尖”不同,与“打尖”风马牛不相及。
如今,贵州省铜仁市的谟望县仍有打尖乡打尖村的古地名延用,想必是在茶马古道上行路,人们在进入某处险要路段或边界之前集中“打尖”,停下休息进饮食,以备气力翻越该路段,久而久之,这些打尖的地段便形成了许多店铺供休息、供用餐,亦或干粮缺失,旅客也必进店而饭,但都不是“投店住宿而饭”。
因此,宿迁人方言中使用并传承的“打尖”这一典型的方言词完全可以正确定义为“在劳作或者旅途中为缓解劳累而短暂休息并且吃点东西的行为”,当然也包括“进饮水”的行为。
作者介绍
朱向东 1956年生,宿迁市宿城区人,江苏省语言学会会员。曾任中学教师、宿迁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。笔名黄墩逐,著有《宿迁方言志》《宿迁方言词典》等。
- 上一篇:层林尽染时逛栖霞山,别错过了这处林则徐诗碑廊!
- 下一篇:陈友兴:垛田名考

